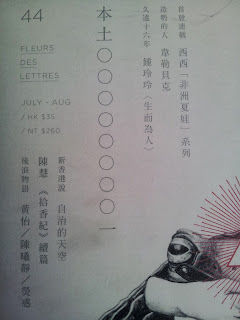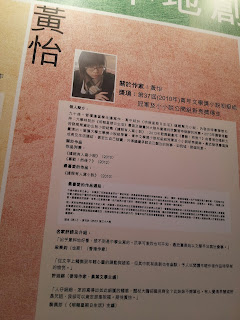(原刊於字花第44期)
在想到最能代表並總結所謂「香港」為何物的物事以前維多利亞林必須先買到一套完美的衣服——她的母親給了她四千元,在今日的香港大概可以買到一襲中等價位的裙子或一套在旺角訂製的廉價西裝吧。時間無多了:慘不忍睹的文憑試已經結束、六月尾的謝師宴日漸迫近,而逃離香港到英國留學的機票亦已訂於八月初,所謂什麼是香港的問題,維多利亞林決定留待事關重大的Grad Din(Graduation Dinner)過後才認真思考。
可是所謂的香港實在是什麼呢?她在Vivienne Westwood裡摸著流行雜誌介紹過的新季格仔西裝褸時仍然不禁想起:我可以帶什麼到英國去向新同學形容我城以及我本人呢?嗯,還是不要分心,為Grad Din選衣服可是無比重要的事,因為這可是她第一次有借口徹底靠近姐姐的形象:出生於姐姐之後讓維多利亞林一直都得穿姐姐的舊衣服,由校服至襪子至柔軟細白的第一件胸衣,在緊貼維多利亞林的皮肉時總仍像帶著姐姐的氣味和形狀,像是生在殖民地城市裡四周都有屬於前朝的異族痕跡——咦,或許這樣的故事或比喻可以帶到英國去冒充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氣氛?可是連維多利亞林的姐姐也年輕得無法生於解殖以前,身為妹妹的維多利亞林又如何能假裝自己經歷過那遠古的年代?
不過維多利亞林又何必理會那所謂的歷史呢。她年輕的身體裡連母親的影子也幾乎看不見。維多利亞林的母親總是那樣典型的母親,肥胖、保守、把自己所認識的無趣人生及狹小世界理所當然的當作可能性的全部並總想像母雞一樣把孩子以及別人都收納在自己的生活模式裡。維多利亞林出生以前英國通過承認同性戀婚姻的法案,當她長大至發現她所處的世界裡人們不只愛異性時,她的姐姐便把她在英國結識的未婚妻和大學畢業證書一起自帶回家。姐姐再次離家前把她的牛津鞋和Fred Perry襯衫都留給維多利亞林,她說,終有一天妳也會想穿的。那時候維多利亞林並不明白。維多利亞是女孩啊。女孩不都是穿裙子和高跟鞋正如香港和中國接壤所以兩個族群的人必定相似,那樣自然嗎。
而姐姐和當時的未婚妻請母親到英國見證她倆的婚禮時她一直閉著眼,彷彿不把眼睛張開,頭髮鏟青如當年仍是少女的G.E.M.那樣的大女兒以及她的同性戀人就不會存在。事後母親再給維多利亞林買來了更多的傘裙和白背心,可是後來維多利亞林在颱風天把姐姐的舊衣服翻出來搭配著玩時,她忽然對於姐姐所愛的密合的褲衩和靠攏的領口有了渴望。原來被衣料細密地包裹身體是如此的溫厚,活動自如並感覺安穩。這就是一直買裙子給我和姐姐和她自己的母親不曾告訴我們的秘密嗎,穿衣而沒有對裸露四肢的羞恥或裙擺讓目光攀越的恐懼,這樣的可能性,如北韓仍未讓國民知道在國境以外的那一切萬紫千紅?
可是維多利亞林不是北韓人也不是母親,她早已和其他的香港人一樣知曉來自世界各地的品牌和價值觀比如對高瘦女生的好評以及經濟自由民主政治的嚮往;維多利亞林路過Burberry時,甚至有想過要不要借Grad Din的名義投資於一件名牌的外套因為不管香港怎樣變幻英倫的同學如何未知,這樣的奢侈總仍會是某種普世價值。她知道每一屆謝師宴裡必定會出現一襲旗袍、一襲及踝長裙和一襲燕尾服,而她知道同學們一直在暗自猜度她會選擇何者。三三四學制讓中學畢業與成年同步,所謂的謝師宴便成了coming of age的宣言;維多利亞林在學校裡一直被高年級的同學標示為「那個穿燕尾服去Grad Din的TB的妹妹」、本人卻從沒有姐姐的英氣和堅毅但也不特別女性化或陰柔因此無法輕易被定義,她知道自己在Grad Din的妝扮將會密合或破滅某些預言,或曰幻想。維多利亞林的姐姐把她的燕尾服也留了給作維多利亞林,可是她的身體不如姐姐的瘦削更貼近母親的厚實和凹凸有致,無法擠進早能容納姐姐的平順剪裁裡。她總無法如姐姐般自如地抱持簡約優雅的紳士氣質,她總是不自覺的過度強調陽剛,或是忍不住表露柔美溫和的性格;她仍喜歡自己的小腿在裙下展現的曲線,然後她會想起母親常穿的那些連身裙,以及母親那圓潤的腳瓜。
她在少女雜誌裡讀到一則愛情金句說,不要和討厭妳母親的人在一起因為最終妳的愛人會討厭妳,這句話暗示的大概是每個妳最終都只會和妳的母親無比的相似,樣貌、性格、習性和話語,而維多利亞林實在不想成為像母親這樣肥胖而老土的婦人。她想要像姐姐那樣擁有棱角分明如歐洲人的面容,卻總發現自己的曖昧和怕事和典型的中國人很像。她沒有讓母親發現自己對姐姐的崇拜,也刻意不在母親面前穿姐姐的舊衣服正如她沒有於四號到銅鑼灣尋找衣飾,因為她知道她母親會以為她去了第四十四年舉辦的十幾萬人集會;她留在家裡故意把電視的音量調高,卻無法告訴在手機和地球另一端的姐姐她沒有出門。而她知道即使她在銅鑼灣,她也不會在維園,而會在崇光。她怕。母親和那什麼,她都怕。
她不想要成為母親,卻總無法成為姐姐。那個專門撰寫愛情金句的作家或許是對的。她開始無法逆轉地和母親愈來愈像。她在Topshop裡搜尋帶著姐姐的氣質的襯衫時仍忍不住把母親喜歡的連身裙拼到身上照鏡,而往鏡裡看時母親遺傳給她的輪廓顯眼得如在她身後打轉的內地旅客們。她試著找尋母親一定不會喜歡的各種方正剪裁和厚重布料,可是通通都和她的胸脯和臀部顯得格格不入;而每當她刻意自母親的形象中逃離,母親的形象顯得更加鮮明龐大,像是此時討論香港仍逃不掉中國卻又逃不進英國,那些像姓氏的前置詞。
她自冷氣商場踏進炎熱明亮的街道,她打顫,一瞬間無法發聲也無法睜開眼,她本能地繼續向前走就能走到哪裡可是她知道前面什麼也沒有。她知道她在跨過那終將要到達的限期後她仍會是學生,在不一樣的國家以一樣的語言考取一張更高級的沙紙,所謂的未來大概就是現在的稍微變調及重覆:她將會和不一樣的路人走在同樣是右面行車的街道上,她會以同樣的名字Victoria結交口音不一樣的同學,然而她隱約知道,她的腳踝將以裙擺而非褲腳作裝飾。
而此刻她的雙手只是恰好仍空無一物。
20130611倫敦